|
1943年6月底至1945年8月底,喬晉樑在重慶擔任中央造幣廠廠長。喬氏,出身山西票號世家,無造幣相關經歷,但任期內因通貨膨脹,造幣不符成本,掌管的造幣廠,卻是處於無幣可鑄的狀態。直到1944年8月23日,因財政部修改「黃金現貨」辦法,將交易單位從一整塊400盎斯美國金磚降至10市兩,切割金磚成為重慶廠的例行業務。(註1) 然而,由美國金磚的供應時斷時續,這項業務也變成時有時無。
1945年6月,傳來消息,對於已延宕多時的大量黃金,美國政府終於同意放行,於下月起將分批運抵重慶。為了應付大量陸續到期的黃金儲蓄與拖欠的黃金現貨,6月23日,財政部下令重慶中央造幣廠必須以每日一萬兩的速度將到運金磚改鑄廠條,最初有十兩、五兩、一兩三種,後來又增加二錢、四錢、三兩三種。這時,喬晉樑與重慶廠的挑戰才真正到來。
根據財政部所下達的目標:重慶廠必須在8月15日之前鑄解各式廠條20萬兩,才能滿足需要。但,遲至8月31日,重慶廠才解交二錢2977條,四錢2814條,一兩7140條,三兩264條,五兩2814條,十兩2567條,總數7萬6千多兩,金條供應短缺的結果,各地紛紛出現擠兌,形成社會問題。喬氏也隨即在9月1日遭財政部下令解職。(註2)
喬氏任內重慶廠無法如期完成任務的原因,於伊始,廠方以各種理由推託,無意負責鑄造有關,本書已有詳細說明。後來,在財政部長俞鴻鈞嚴詞於7月7日警告後,因驚覺事態嚴重,廠方因此改變態度,積極進行。不過,即使如此,向中央印製廠借用宿舍改建廠房、從成都分廠借調機器設備、委託二十兵工廠將金磚輾軋成金條,相關準備在在需要時間,此時已是時不我予。
7月11日,重慶廠向財政部呈報將採用以下工法鎔鑄金條:首先將金磚委託二十兵工廠軋成二、四、六釐米厚度的金片,分別裁成一、三、五兩三種金條;裁切所剩下的邊屑,則以馬夫爾爐鎔鑄十兩條。四錢、二錢兩種,從8月11日起開公,因無法舂製,必須改以手工剪切而成。(註3)
一、三、五兩以及後來增鑄的六兩條等四種,是以機器輾軋裁切;十兩條,以馬夫爾爐鎔鑄;四錢、二錢,則是以手工裁切,重慶廠條主要就是使用這三種工法鑄造而成。除此之外,重慶廠還曾將部分裁切剩下的邊屑鎔化後澆鑄成金餅,這是一種未見於先前報告的傳統工法。 這種重慶金餅,只見過一兩型,原僅收錄於檔案圖片-正面:「國民黨黨徽,中央造幣廠造」、背面:「CK7859,成色997.0,重1.088市兩」(見Fig.1-3),最近在市面另出現一件-正面:「CK4989,成色996.4,重1.001市兩,中央造幣廠造」(見Fig.4-6_(註5),可確定曾經從造幣廠流出。因此,筆者在《廠條,1945-1950》另追加其編號為 “Ckx”。從號碼順序可知,這種重慶Ckx金餅鑄於1945年8月下旬,應是為了增加金條產量而來,但隨著其去職,9月上旬就告停鑄,成了喬廠長的告別之作(註4)。兩相比較下,這兩個金餅,出現先後有別,特徵存在差異,廠方顯然正在進行改良。較早的CK4989,做工簡易,呈不規則的橢圓形,尚無徽章標記;較晚的CK7859,改採雲南、四川銀樓常見的金餅模鑄,造型規整,另外,也開始出現了圖案。不過,並不是代表財政部或中央造幣廠的布圖,而是國民黨黨徽。這個設計頗為唐突,加上,欠缺副字軌(sub-prefix) 重慶廠一兩金餅並未持續鑄造,或許就是這些原因。
(註1)Stephen Tai, The Gold Bars of The Central Mints, p.26 (註2)ibid.,p.35 (註3)ibid.,p.39-42 (註4)ibid.,p.45-46
(註5)GBCA官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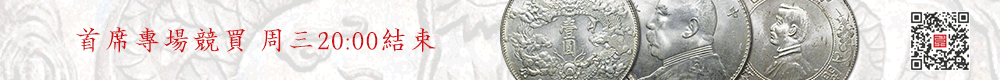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首席收藏
( 京ICP备11006322号-8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首席收藏
( 京ICP备11006322号-8 )